 在北京星海钢琴集团卧式琴大师工坊内,一位梳着齐耳短发、戴着细框眼镜的工匠正俯身在一架九尺三角钢琴前。左手轻击琴键,右手握着调音扳手,耳朵微微侧向音板——这个姿势,王英已经做了32年。从油漆工到全国优秀钢琴调律师,从普通工人到卧式琴大师工坊负责人,王英用30余年时间,在88个黑白琴键间,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之歌。
在北京星海钢琴集团卧式琴大师工坊内,一位梳着齐耳短发、戴着细框眼镜的工匠正俯身在一架九尺三角钢琴前。左手轻击琴键,右手握着调音扳手,耳朵微微侧向音板——这个姿势,王英已经做了32年。从油漆工到全国优秀钢琴调律师,从普通工人到卧式琴大师工坊负责人,王英用30余年时间,在88个黑白琴键间,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之歌。
1992年夏天,18岁的王英站在北京钢琴厂招工报名处,她清澈的眼眸里跃动着对钢琴的渴望。从小在《东方红》钢琴旋律中长大的她,父亲工会活动室里的二胡、笛子是她最早的音乐启蒙。“当时就想离钢琴近一点,哪怕只是给钢琴刷漆。”回忆起入厂初衷,王英眼里仍闪着光。
油漆车间是钢琴制造的第一道工序。夏季,车间温度高达40摄氏度,王英要戴着三层口罩给钢琴外壳打磨上漆。“因为油漆的厚度会影响音板振动,每道打磨工序都关乎最终音色。”王英在师傅指点下,逐渐悟出“漆工也是调音师”的道理。下班后,她总溜到总装车间,看老师傅们如何将零部件“变”成钢琴。凭借着对钢琴的热爱,1995年王英转去调律岗位。
在如今的北京星海钢琴集团卧式琴大师工坊里,悬挂着数十把不同规格的调音扳手,每一把都记录着她从学徒到“大工匠”的蜕变。回想当年学习阶段,王英每天要花数个小时趴在钢琴前,用音叉反复比对每个音组的440赫兹标准音高。前3个月,调音的枯燥也曾让她想过放弃,但不服输的性格让她不愿放弃。终于,在3个月后的某一天,她突然能听出调音扳手与音律之间的变化。之后,她对调音的热爱,一发不可收拾。随着调音技术不断提升,为突破瓶颈,她曾连续2个月每天聆听6个小时和弦分析泛音,最终练就了同时捕捉5个以上谐波的听觉解析力。
2000年,星海集团接到人民大会堂十五英尺超大型卧式钢琴修复任务。此时,年仅26岁的王英凭借在厂内技能内测比赛中连续3届荣获钢琴调音前三名的优秀成绩,入选修复团队,负责钢琴调音任务。为1949年全手工制作的“国宝级”钢琴进行修复,难度可想而知。“当时给我们的要求是‘原样修复,修旧如旧’不能更换任何部件,只能在原有基础上修复。”王英回忆道。还原88个弦锤的原始弧度,且不能更换弦锤,王英只能在原有磨损严重的老弦锤上重新修型。数十年弦锤敲击羊毛毡老化,王英用砂纸每打磨一下,就产生大量羊毛纤维,飘满整个修复室,毛毡的不稳定性导致修复难度大幅提升。从3个小时修复一个弦锤,到最后仅需1个多小时,88个弦锤的修复,让她练就出弦锤修复的肌肉记忆,并总结出弦锤修型快速修复法。短短2个月的修复任务,成为了王英职业生涯的永恒标尺。
“调律不仅是技术,更是与钢琴的对话。”王英常对徒弟们这样说。夜幕降临,王英为明天要交付的三角钢琴做最后校验。当《我的祖国》的旋律在试音间流淌出来,那些在油漆车间的青春、人民大会堂的羊毛絮、比赛前手上的老茧,都化作了琴弦上跳动的音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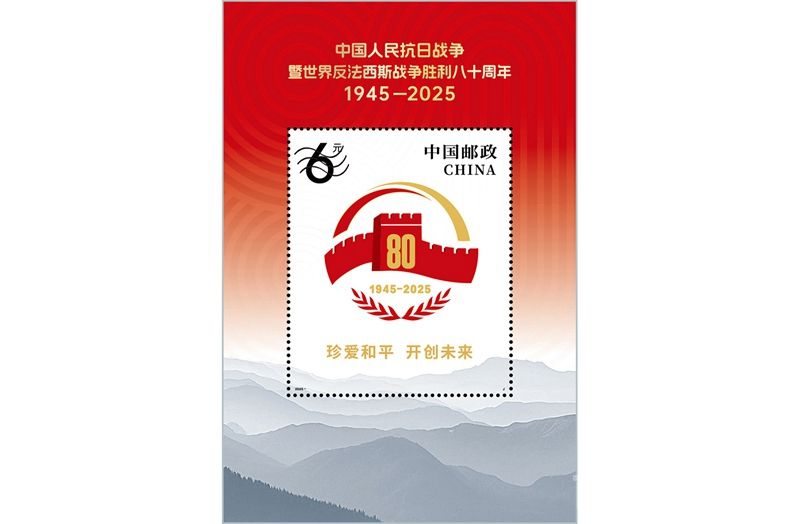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